
作者 | 天雅
在生活中,有这样一类人:
他们长期停留在一段受虐关系中,迟迟不离开。
你若问他们“为什么不离开”,
他们会给出很多明面上的理由:身上没有钱,孩子还小,离开后不知道去哪里……
有时在经历完一场来自伴侣的严重暴力后,他们会信誓旦旦地说要离开。
可等情绪稳定下来,面对伴侣的假意道歉与认错,他们又会重新回到伴侣身边。
你若问他们“为什么要回去”,
他们多半会回答是因为“爱”:感觉伴侣还爱着自己,而自己,也还爱着伴侣。
身为一个局外人,我们或许很难理解:
为什么他们会将一段充满伤害的暴力关系,理解成是“爱”?
可一旦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,我们会发现,一切有迹可循。

前几天,我家里发生了一场离婚闹剧。
我妈给我打电话,说实在受不了我的继父,想要离婚。
我很支持她。
我的继父是一个文化低下、生性多疑、脾气暴躁之人。
他经常会没有缘由地怀疑我妈出轨,对我妈进行喋喋不休的羞辱。
有时我妈回怼他两句,他脾气一上头,就会忍不住对我妈动粗。
我妈心里有很多委屈,经常在我和我弟面前诉苦,控诉继父的种种不是。
我曾经问过她:“你为什么不离婚?”
她说:“离婚了就没法供你和你弟上学了。”
后来我和我弟都从学校毕业了,而我妈也跟我继父分居多年,各自经济独立了。
我继父每天都会对我妈进行电话轰炸,随时随地监控她的行踪,稍有不爽就会对她进行羞辱和诅咒。
我妈不胜其烦,但依然没有离婚。
我问她为什么不离,她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。
我隐隐约约有一种猜测:她可能并不想离婚,也不想彻底结束这段受虐关系。
而这次的离婚闹剧,进一步验证了我的猜测——
几天后,我发信息问我妈:“离了吗?”
她回了一句:“这事急不得,慢慢来。”
然后,整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

回顾我妈的前半生,她其实具有很强的「生命韧性」:
能够在两段糟糕的婚姻中坚强地存活下来,并将我和我弟抚养长大,
后来跟我继父分居以后,她又白手起家,独当一面,将生意做起来。
但她却很难离开一段有毒的亲密关系,彻底从“受害者”角色中走出来。
这是为什么呢?

无法离开一段受虐关系,换而言之,就是对暴力具有很强的耐受性。
要探讨为什么无法离开,就得追溯:这份对暴力的耐受性,它来自哪里?
从心理学层面来讲——
它多半来源于:一个人在童年时期,对身边某个暴力客体的依赖与认同。
我妈就像是这一种情况。
她出生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多女子家庭,家中有一个脾气暴躁的祖母。
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,她基本得不到来自父母爱的滋养。
在成长中的很长一段时间,她都是在祖母的羞辱和打骂中度过的。
直到后来,祖母年纪大了,干活干不动了,
我妈通过帮年迈的祖母干活,换取到了生命中罕见的一丝爱与看见。
后来逐渐地,祖母越来越依赖她,将她视为自己的“小女儿”,会在她生活困难时主动给予情感支持和物质帮助。
两人建立起了微妙的“母女之情”。
这样一段错位的“母女关系”,构成了我妈生命中亲密关系的原型,也持续影响着她对「爱」的感知。
在她的观感体验里——
亲密往往伴随着暴力;
爱不是无条件的,它需要付出、忍耐甚至牺牲,且常常伴随着痛苦。
从某种意义来讲,她跟我继父的关系,就是她跟她祖母关系的重现。
她不想跟继父离婚,因为她害怕失去那种“既痛苦又熟悉”的关系。
或许在她的感受里,哪怕在关系中被羞辱,也比独自一人坠入没有爱的孤独深渊好。
这是一种心理上的“安全区”,尽管充满了伤害,但那是她唯一知道如何生存的地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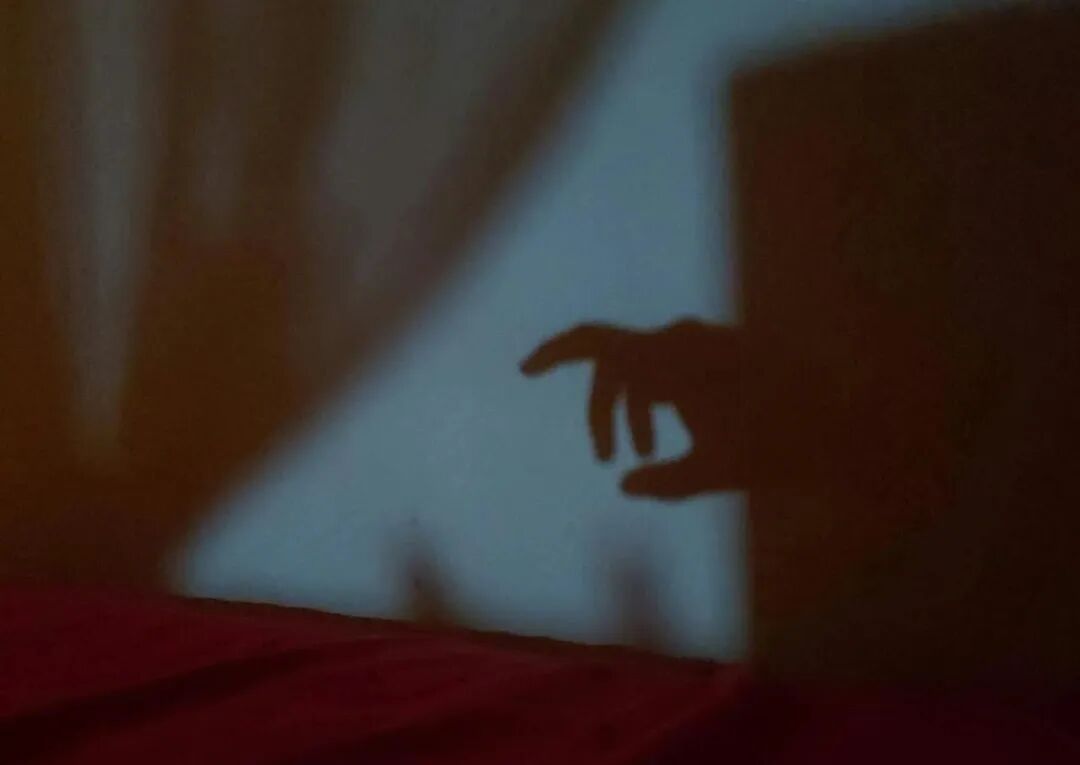

我跟我妈一样,成长过程中都缺少来自父母爱的滋养。
我的父母在我3岁那年离异了。
父母离异前,我跟奶奶一起生活;父母离异后,我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。
我的奶奶同样是个脾气暴躁之人,经常会没有缘由地冲人发脾气。
但唯独,她从不打我,也不骂我。
而我的外公外婆,则是一对性情温和的恩爱夫妻,两人从不争吵。
这也意味着——
在我生命早期的亲密关系原型里,是不存在“暴力”这个选项的。
我所体验到的爱,它是温和的、包容的,且不存在任何交换条件。
记得大三那年,我去我妈和继父所在的城市打暑假工。
期间由于忍受不了继父喋喋不休的控制欲,我回怼过他一次。
从那以后,他开始把我当“刺头”,处处对我进行嘲讽羞辱,
甚至在我膝盖被玻璃刮伤时,他不仅不给钱我去看医生,还将我大骂了一顿。
我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毫无同理心的暴力之人,不愿再跟他进行任何往来。
于是大四以后,我靠勤工俭学养活了自己,再也没去过他的家,也没伸手向他要过一分钱。
我之所以能比我妈更早摆脱一段“受虐关系”,并不是因为我比她更强,
而是因为我跟她有着不同的成长路径,不同的生命体验,以及不同的对爱的感知:
在我妈的感知里:爱,往往伴随着暴力;
而在我的感知里:暴力,它从来不是爱。
这也从侧面反应了,一个人在长期受虐中形成的生存模式,是多么根深蒂固,多么难以撼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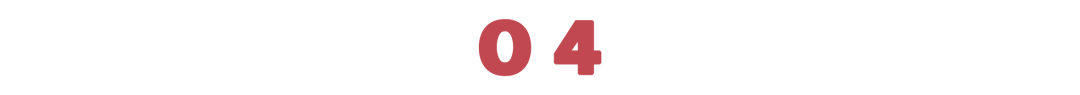
在《豫见她们》第一期——
作家兼心理咨询师张春,谈及一些极端案例中的家暴受害者。
她说,
受害者离开一段暴力关系,不是一瞬间的事。
Ta其实要做很多准备,比如说她要先有一个银行卡,或者先有一个独立抽屉。
因为很多受害者是被伴侣全方位控制的,没有任何自己的空间。
Ta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抽屉,就是一种进步。
Ta可能需要用10年才能做到完全离开,但这是一个过程。
她的话道出了施受虐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真相——
很多时候,施虐者和受虐者是共生在一起的,他们相互需要,彼此依赖。
施虐者用暴力来掩盖自己的脆弱,用控制来填补内心的空洞;
而受虐者则用隐忍来逃避孤独,用牺牲来换取“爱”的幻觉。
他们彼此需要,却又彼此伤害——
就像两棵相互缠绕的树,在共生绞杀中维持着一种扭曲的平衡。

一个受虐者,要想真正从一段暴力关系中觉醒并逃离,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,
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年,甚至更久。
因为期间Ta要面对的不只是外在的暴力,更是内在的恐惧、羞耻、无力和绝望。
Ta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自我剥离过程,日复一日地在内心种下一点一滴的觉察:
当Ta开始意识到“我值得被尊重”,
当Ta开始相信“我的感受是重要的”,
当Ta开始为自己争取一点点空间,哪怕只是一个抽屉……
这不是简单的空间,
而是一个人开始找回自我、重建尊严的起点,是Ta内在生命力的苏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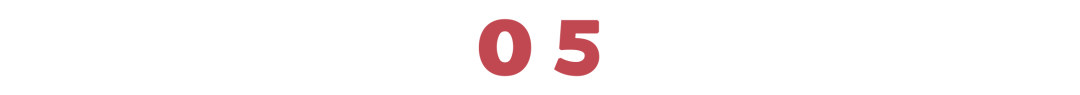
写到这,我仿佛进一步理解了我妈。
这二十多年来,她看似一直停留在一段充满暴力的婚姻关系中,迟迟没有离开。
但事实上,她并非止步不前,而是在以自己的节奏,缓慢地向前蠕动着:
从一开始作为一名全职家庭主妇,完全依赖继父的物质供给;
到后来她跟继父一起创业,成为一个负责统筹规划的老板娘;
再到后来她跟继父两地分居,白手起家,独当一面,再创业……
或许她正在用自己的方式,努力争取属于她的银行卡和抽屉,
继而将自己从那个被控制、被剥夺、被压抑的受害者角色中,一点点剥离出来。
我无法用自己的体验去代替她的体验,也无法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她的选择,
我唯一能做就是:理解她的痛苦,尊重她的节奏。
她能在两段糟糕的婚姻中存活下来,将我和我弟抚养长大,并在跟继父分居后重新站起来,这些都是她内在力量的体现。
她暂时无法离开婚姻,不是因为她软弱,而是因为这段婚姻已经成为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,是她情感世界中熟悉的感觉。
在理智上,我们都知道,离开痛苦的关系就是解脱。
但在情感上,对她而言,离开还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的未知和恐惧。
或许她还没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,她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,等待自己内心深处的觉醒。
相信未来有一天,她会越来越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内心需求,继而做出独立成熟的人生选择,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生命道路。
祝福她。

作者:天雅,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,广州心协三级心理咨询师,自体心理学长程在读。本文原创发布公众号:武志红(ID:wzhxlx)。

从受虐关系中走出来,往往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内心重建。这需要打破旧有模式,重新学习什么是真正的爱。
如果你正在类似的关系中挣扎,感到被困住而无法挣脱,武志红心理咨询中心可以提供专业支持。
心理咨询师陪你一起梳理混乱的感受,看清关系真相,重建受损的自我价值感,为真正意义上的离开或关系转变积蓄力量和资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