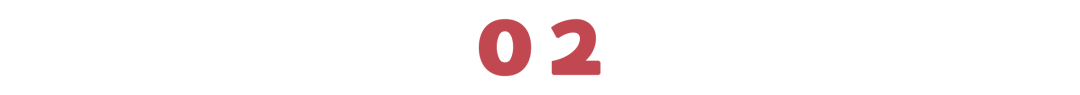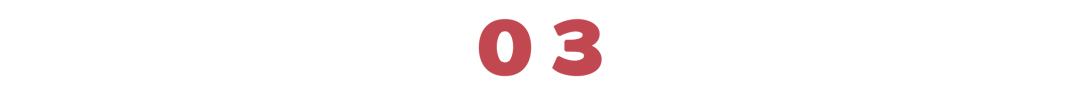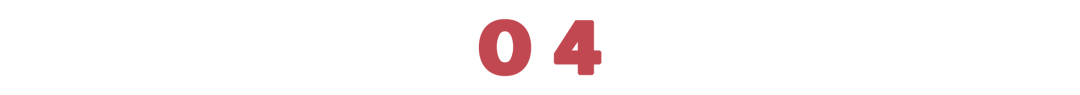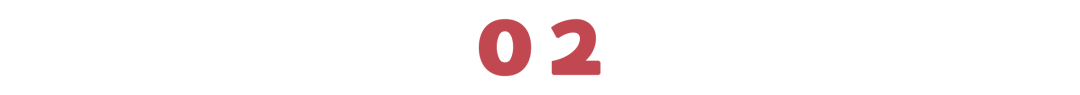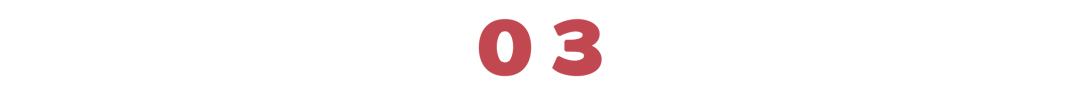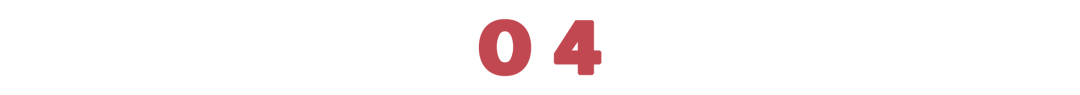作者 | 张倩
编辑 | 陈沉沉
推荐一部2023年迷雾剧场出品的新剧: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。
这部同名小说改编的连续剧,结构非常紧凑,只有6集。
从审美层面来说,这部剧把悬疑和文艺结合了起来,无论是叙事方式、镜头、剧名,都非常有风格,也因此获得了73届柏林电影节剧集单元提名。
而在这部剧的前半部分,更能带给我们心理学上的思考——
一个孩子,在养育环境缺乏滋养的情况下,如何寻找外在的回应和共鸣,最终成长为自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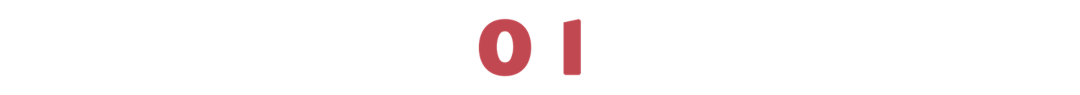
这个孩子,自幼上学开小差、打架,隔三差五被安排见家长。
小树成长为一个无所事事的叛逆少年,跟父母有很深的关联。
她和丈夫庄德增结婚前,提出一个要求是:不要干涉她读书。
但是作为一个国营厂职工,她却无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
除了清高和独来独往的秉性使然,她也的确存在一些人际上的困难——
这样的一个妈妈,别说照顾儿子小树、给予他关爱,她甚至很难全身心投入到关系里。
在小树三周岁时,她才发现自己的丈夫,是多年前打聋父亲的其中一人。
另一方面,她已经和这个仇人成了家,还生下了一个孩子,一切不可更改。
她把自己过得像个独身女人,既不理会丈夫,也不照料孩子。
此后不久,更是只身一人,离开了一直和丈夫、儿子共同生活的城市。
只要不看两父子,她就不必去面对,和伤父仇人结婚的屈辱事实。
于是,儿子小树的存在本身,也成了傅东心想要极力否认的一部分——
她需要视而不见这个孩子,才能让自己内心没那么冲突。
小树闯祸了,她默不作声;老师让领人回家,她就一声不吭领回家。
可是,相比于对小树的视而不见,她对邻居家的孩子小斐却十分热情——
她像一面破损的镜面,照不见小树作为一个生命的独特。
不幸的是,像每个孩子一样,童年时期的小树没有能力去解读,妈妈为什么会如此否定自己。
因为我不够好、我不值得,所以妈妈不够爱我,更没法回应我。
当一个孩子如此诠释妈妈的行为,就会产生很多连锁反应。
他可能自尊不足、人际疏离、内心空洞,对世界无所适从,甚至还可能发展出病理性的自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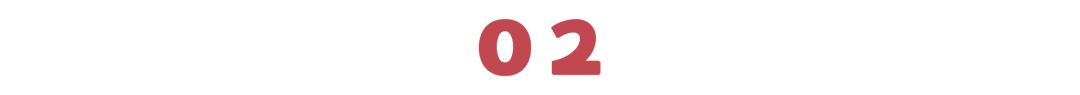
相比于妈妈的否认退缩、忽视漠然,小树的爸爸庄德增显得可以“搞定一切”:
即便小树打架再多,都有爸爸撑腰周旋,而得以回到学校;
爸爸像“超人”一样,因此小树可以不必优秀,甚至不用为自己负责。
偏偏这么头脑聪明、行事活络的爸爸,却不被妈妈欣赏。
甚至,在家里爸爸成了一个同样被忽视、被冷漠对待的“失能”男人。
从心理学角度理解, 小树没有了 理想化的对象 ——
一个孩子要长成自己想成为的人,在成长的早年时期,需要一个理想化的对象(通常是养育者);
这个对象承载着一个孩子未来努力的目标,和一生的价值感。
所以,一个既缺乏母亲温暖的回应,又没有理想化对象的孩子,内心是空洞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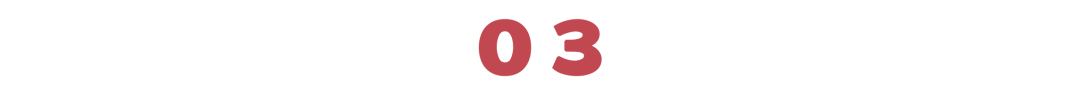
本剧的第三集,叫《37385》,这是一个警员的工作编号。
这个警员非常年轻,他抓住了再次打架斗殴的小树,企图用正义感、一心保家卫国的激情感化小树:
这话像是一颗投进湖里的石头,荡荡漾漾泛开一道道波纹。
37385号警员的郑重其事,是他从父母那里从来没有感受过的——
妈妈只会忽视他,否认他的存在,他在妈妈那里是个不学无术的“惯犯”;
爸爸溺爱他,却从来粗心大意,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尊严的大人去对待,他在爸爸那里是个“比一般人还一般的人”。
后来,因为老爸庄德增能干,小树又一次从局子中被捞出来。
他坐在警局的长椅上,向另一个警员询问37385号警员的去向,却被告知,后者因为坚守这个城市的安全,已经被歹徒捅死了。
他这才明白警员的正义、严肃、认真,和他嘴里所说的“牺牲”和“保护”,究竟为何物。
一个人原来可以活得很有意义,既不必像妈妈一样的疏离退缩,也不必像爸爸一样做个万金油。
他找到了一个能照见内心的人,那同时又是一个理想化的对象。
而这种深入内心的共鸣,就是自体心理学说的, 「自体客体体验」 。
带着这种全然不同的体验,小树去考了警校,经过几年学习,成为了一名追求真相和正义的警员,一步步成为了他自己。
而尽管后来小树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,因为时代、命运和所付情深,又遭受了一次重创,却无法抹杀,他找寻自己所做出的努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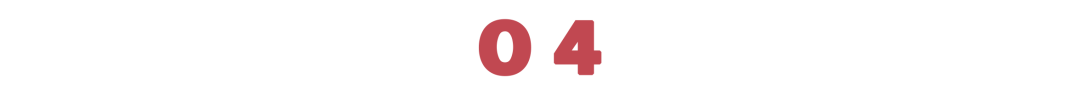
其实在《平原上的摩西》,讨论的远远不止是父母对我们的影响,更是时代、苦难、命运、救赎和深情……
而这段关于小树的成长与改变,仅仅用了不到四分之一的笔墨。
有一个不能温暖回应我们的妈妈,或一个无法作为榜样(理想化对象)的爸爸。
最终, 一些人长 期处于空洞和迷茫之中——自我无处安放,时时刻刻都不知如何是好;
而另一些人则发展出了自我,有了自己的方向,能够确认自己的独特性和意义感。
区别在于,你是否在后续的生活中,找到了你原生家庭所缺失的「自体客体体验」。
即,与你钦佩的人相连接,产生一种平静、抚慰、安全、有力量或有激情的体验。(Peter,2017)
因为没有理想化的过程,他们难以调节自己对外界的焦虑和恐惧,更无法在生活和学习上发展自己独特的目标。
在咨询过程中,帮助他们激活内在的共鸣,体会理想化自体客体的体验,尤为重要。
科胡特提到,理想化的过程一旦完 成,便可以发展出一个人的理想。
人的一生都有这样的 需要,特别是沮丧和恐惧的时候。
但当我们内在获得足够的自体客体体验,就不再那么依赖外界去给予。
当然,并非有了理想化对象之后,我们的生活就万无一失。
就像很多孩子,最初都觉得父母或榜样十分厉害,但随着自己成长却发现:
就像影片中的小树,他将警员视为自己的理想化对象,但也在破案的过程中,同时体会着警察的无力与受挫。
也像在咨询中,最初来访会觉得咨询师对自己很理解,逐渐地也发现咨询师并不时时刻刻、全部理解自己。
也就是说,即便我们被恰当的回应,拥有了理想化对象,我们依然会经历失望、受挫的时刻。
而恰恰是这种时而被满足、时而受挫的体验,慢慢锻炼出我们更真实、更适应世界的内心:
我们不可能在每一时刻都获得深深的共鸣,但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一部分体验,也有能力体会他人的一部分体验。
作者:张倩,心理咨询师,自由撰稿人,预约心理咨询请点击下方卡片。
本文原创首发公众号:武志红(ID:wzhxlx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