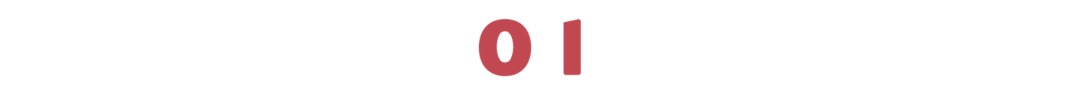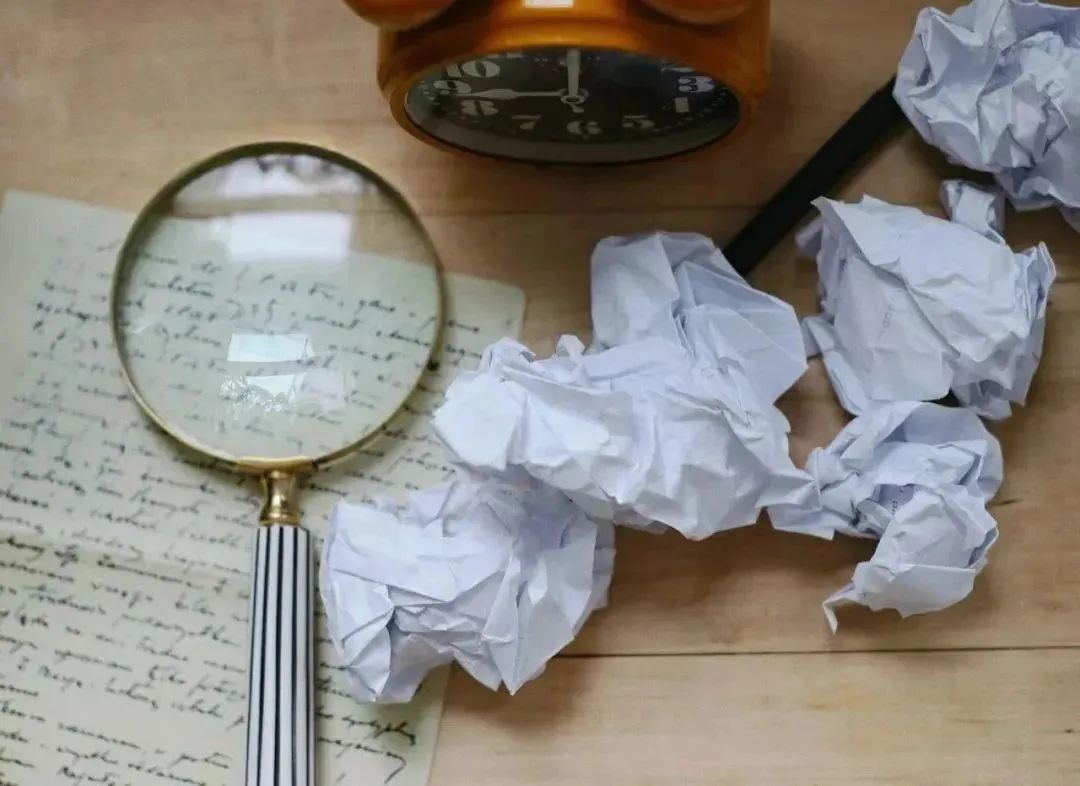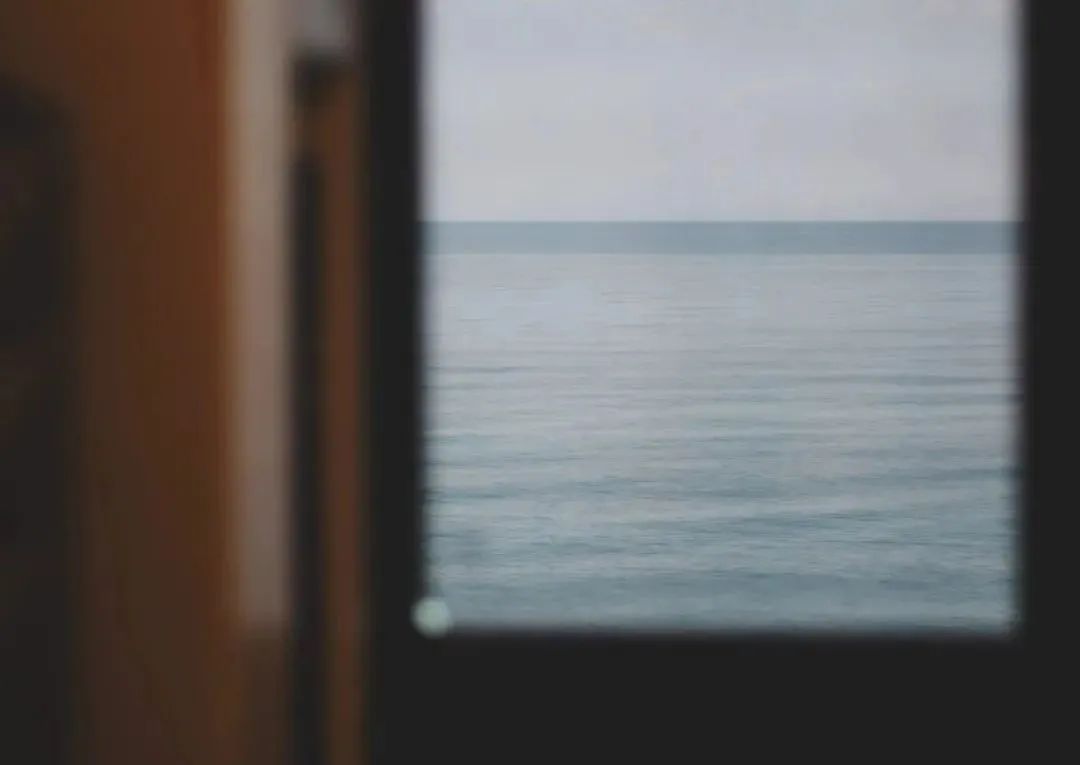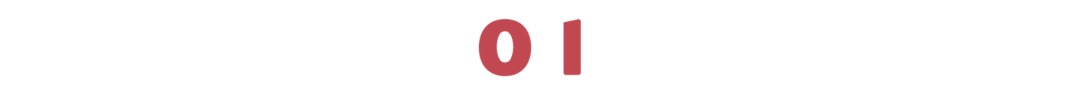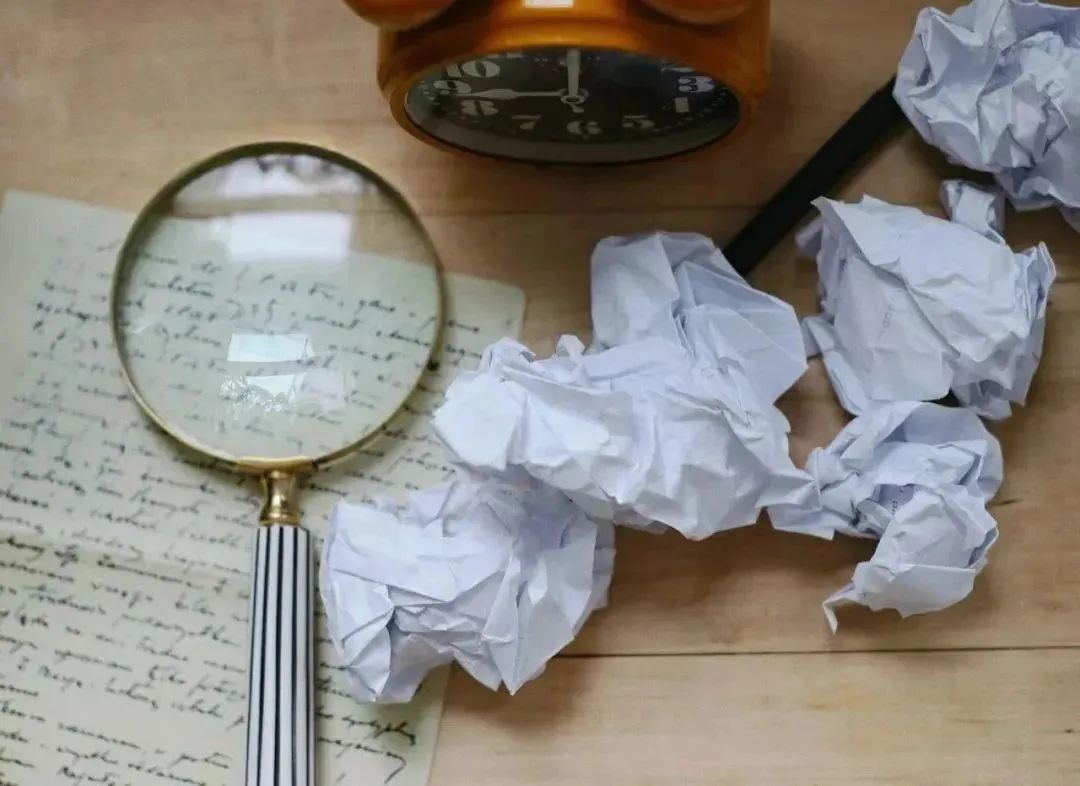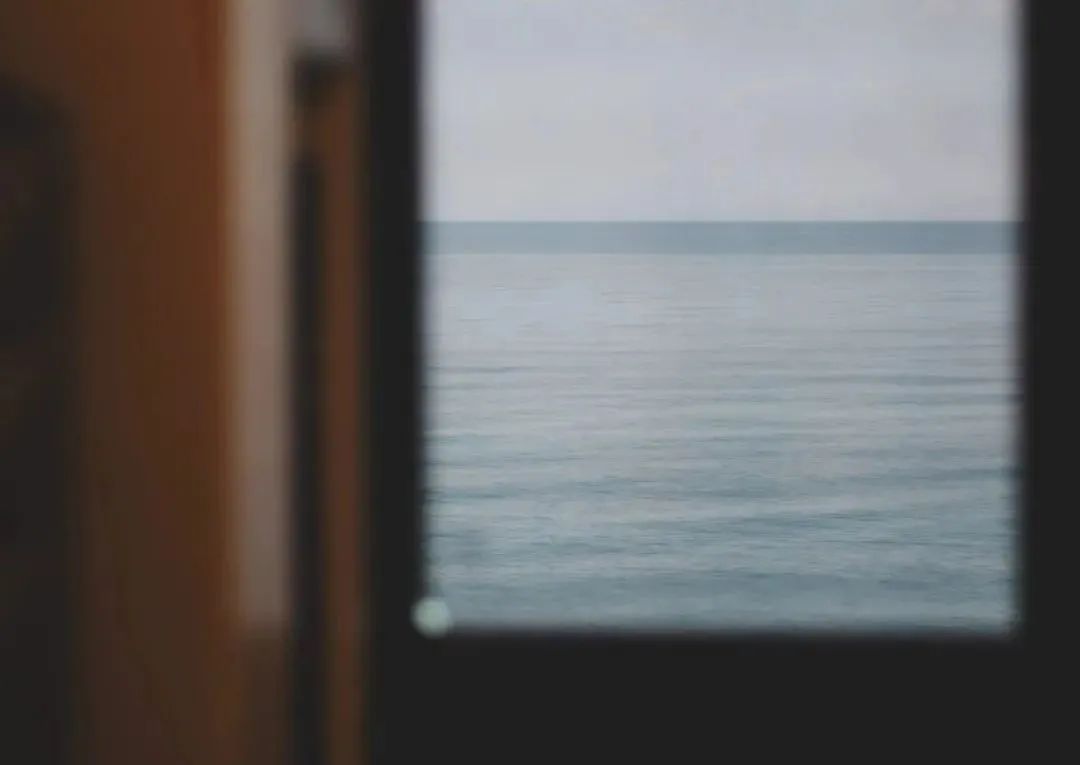当他人遭受不公对待,他们会不管三七二十一,坚定地站在“受害者”一边,伸张正义。
但与此同时,他们却很容易在关系中误伤他人,搬弄是非,将矛盾不断激化、扩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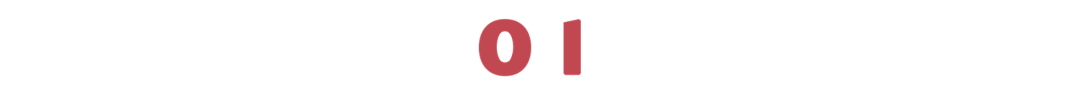
李阿姨是一名社区管理员,也是出了名的“正义使者”,常常替邻里街坊主持公道。
包括很多街坊,在与他人发生矛盾冲突时,也经常找她来处理问题。
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,却令我对李阿姨的正义感产生了「质疑」。
高血压老人中风的概率,确实比平常人高,不吃降压药,风险会更大。
如果好好关照老人身体,阻止她停药,或早点送医院,也许老太太就不会中风了,或者瘫痪程度会有所缓解。
但我却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对劲,虽然说不上哪里有问题。
她正在以张家作为反面教材,教育年经一代要孝敬老人,言辞间充斥着对张家子女的不满与愤怒。
在她的描述下,张家子女仿佛成了“十恶不赦”的罪人——
自私自利,情感淡漠,甚至为了省钱,故意让老人生病。

是指当不幸事件发生以后,人们常常会习惯于寻找一个「罪人」,去指责TA,甚至惩罚TA。
120没来之前,在路过医生的帮助下,替张先生做人工呼吸和人工按压。
但半个月后,她却被张先生家属告上了法庭,索赔60万。
甚至有时候,哪怕不是事件的直接关系人,而是一名局外人,
我们也有可能会不知不觉地,陷入到「寻找罪人」的游戏中。
面对受害者时,我们心中会萌生出一股拯救他人的正义感,并试图通过“惩罚加害者(罪人)”来伸张正义。
当我们真正这样做的时候,我们觉得自己跟加害者(罪人)完全拉开了距离,成为了充满光明正义的拯救者。
如果 找对了加害者(罪人),我们为了公平正义去声讨TA,惩罚TA,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。
比如面对一个杀人犯,我们呼唤严厉制裁他,这并不为过。
但如果 ,找错了加害者(罪人),然后我们以“对”的名义去攻击TA,那结果将会很不同。
我们可能会伤害到无辜的人,令他们成为了受害者,而我们自己,则会变成加害者(罪人)。
但在李阿姨的视角里,张家子女却变成了加害者(罪人),原因是他们没能提前阻止悲剧的发生。
当她带领邻里街坊去声讨张家子女,并不惜为此夸大其词、搬弄是非时,
她自己就变成了加害者,而张家子女,则变成了受害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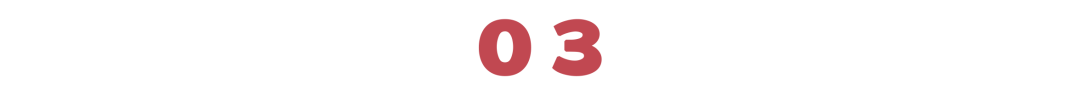
在现实生活中,并非所有的不幸事件,都存在一个加害者(罪人)。
有时候,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意外,或是受害者自主选择的结果。
如果我们执着于伸张正义,陷入「寻找罪人」的游戏中,
其结果,不仅会违背自己的本意,还会给无辜者造成误解与冤枉。
所谓课题分离,就是区分什么是你的课题,什么是我的课题。
我负责把我的事情(课题)做好,你负责把你的事情(课题)做好。
作为局外人,我们真正能做的,不是越过界限,去替受害者出头,去替TA声讨加害者(罪人),而是:
客观看待事件的前因后果,尊重受害者本人的意愿,在能力范围内提供资源或帮助。
这个过程,需要我们诚实地 觉察自己内在真实的动机。
有一回,我跟男友因为一点小事闹矛盾,心里郁闷,找她倾诉。
还没等我把话说完,她就开始愤怒地指责我的男友,将他批得体无完肤。
“他一点也不迁就你,我劝你还是尽早分手吧,你值得拥有更美好的关系。”
她坚定地站我这边,并提供了解决方案,看起来很“仗义”。
因为整个过程,她并没有耐心去了解我跟男友发生矛盾的前因后果,
而是代入了很多她自身对男性的愤怒和不满,借题发挥去攻击我的男友。
与此同时,她也不询问我本人的意愿,就迫不及待地劝我分手。
而是想借这个事件,去表达她对男性的愤怒,并惩罚男性。
她过去曾经遭受过一些情感创伤,令她不太信任异性和亲密关系。
一旦听到女性跟异性有矛盾冲突,她过去的创伤就很容易被唤起,并牵引着她去攻击异性。
拒绝她的建议,并基于我自己的本心,去跟男友进一步沟通,化解矛盾,修复关系。
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在不幸事件面前,去无视受害者,或拒绝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在我们决定为受害者匡扶正义之前,先去诚实地问自己一句:
我这么做,到底是为了成全TA,还是为了成就我自己?
比如想当个「拯救者」,想借此抒发对「加害者」的不满与愤怒等等,
而是要先去了解自己内在未被满足的需求、匮乏与缺失,
作为一个成年人,我们需要先为自己的需求去做一点事情——
满足自己的渴望,照顾好自己,为自己的需求负责,安慰自己内在的不安。
便会有足够的理性与智慧,去看待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,
看见受害人真实的处境与意愿,提供能力范围内的有效帮助,促进事情的圆满解决。

天雅,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,广州心协三级心理咨询师。
本文原创首发公众号:武志红(ID:wzhxlx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