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:
被当做家庭血包的孩子,
努力赚钱,接着往家里不断地送钱,
然而血包只是工具,不是人,
因此没有作为人的自我意志和完整主权。

父母总是在要钱
好累,要不要给?
最近好友来向我求助,关于「该不该给父母钱」的问题。
她是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,学业事业的突破,帮助自己实现了跃迁。
过去经济收入还不错,她对父母很大方,每月定期汇款,节日还有礼物红包,一年也带他们外出旅游两趟。
但最近几年,自己有了房贷,还生育了两个孩子,市场收缩,无法再像之前那样为父母一掷千金。
但父母总是一边向她索取,一边抱怨她抠搜。
最痛苦的是,她妥协给了之后,父母还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要。
而且是用一种理所当然、看似不容拒绝的方式索取——
“我生病了,你去交一下我的医疗费用吧。
“房子太破了,住不下去,装修费你来给吧。”
每一次索取带来的内心挣扎和痛苦,都在提醒刺痛她:
在父母眼里,她不是活生生的女儿,而是一个提款机。
于是,她产生了一个念头:想一次性给父母一笔大钱。
以此希望:他们不再反复地找自己索要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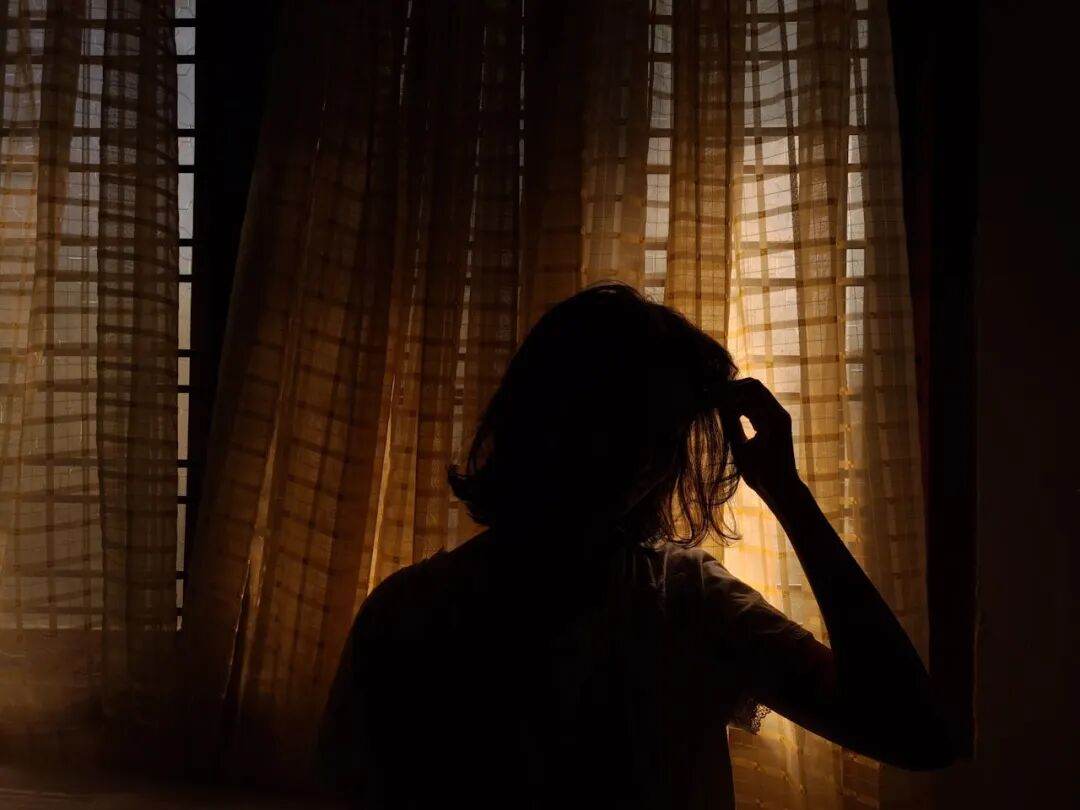
这样想法看起来突兀,但很多创伤来访都有过类似的。
他们想努力赚钱——给父母钱——然后或短暂或彻底地远离他们,远离压力应激源。
本质上,是想通过给钱,“买断”或“赎回”自己的自主空间。
他们大多从小没有被善待,是家里最被忽视的孩子。
幸运的是,自己足够强大,发展了出来。
在有了经济能力后,父母开始靠近他们,
但这种靠近不是出于爱和补偿,而更多是干涉和索取。
也许看到这里你会感到愤怒,质问为什么不直接拒绝?
对于这个问题,他们是回复不上来的。
每一次和父母的接触,他们都会感到莫名其妙的疲惫:
一方面,他们隔绝不了父母的情感绑架。
父母每一个干涉和索取的言行,都会激发他们过去被忽视的伤痛和强烈的愤怒。
但另一方面,他们又割舍不下父母投来的关注,因为他们过去从未得到过;
或者是担忧父母、兄弟姐妹其中的一员,担心自己的拒绝和冷漠伤害到他们。
所以这种愤怒,是被深深压抑的。
他们只能感觉到很痛苦、很挣扎、被互相矛盾、错综复杂情绪拉扯着,累到不行。
给钱,是展现自己的价值,
以此证明父母过去对自己的轻视是错误的;
给钱,也像是一种“断臂求生”的无奈之举。

不断给钱,把自己交出去
心理咨询师付丽娟曾写道:钱是我们自我的延伸。
当父母过多的索取,而孩子不能拒绝时,一次一次的妥协,会让孩子感到正在失去自我主权。
这个失权的过程,不是父母单方面造成,而更像是一种系统的共谋:
首先是环境。
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,就听到各种故事:
谁谁家的孩子出去赚钱,每个月给父母交多少钱。
尤其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女性——
一个女儿有多好,就取决于她多大程度上交她的钱,以及她对照顾父母有多么义无反顾。
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孩子,内化了「给钱=我好」的信念。
当我的价值是靠钱来体现时,不给父母钱,就等于「我失去了价值」。

其次是父母。
父母默认孩子的钱就是自己的钱,养你就是为了以后你长大后能够养家。
父母和环境共同把孩子工具化——
你属于这个家,不属于自己,你的钱一样。
当然,这其中最重要的是,孩子自己是否认同?
有的孩子“很自私”,守住自己的钱,是父母眼里的抠门铁公鸡,一毛不拔。
但你也同时看到,ta没有认同系统施加的压力,守护了自己的金钱边界。
而有的孩子,很早就开始认同系统对自己“估值”:
如无法满足父母,我就没有价值,因此要不断给出。
在网络上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视频,一个28岁的女孩和妈妈一起去买鞋,女孩看中一双200块的鞋子,父母觉得太贵想走。
女孩跪下歇斯底里地喊:
我每个月工资都给你了,200块的鞋子都不能给我买,我的脚这么廉价吗?
一个成年人,丧失对自己金钱的支配权,同步丧失的,是ta的精神自我——
我算什么?我是不是不配?
其中的自我定义权,从来都不在自己手上。
而更加糟糕的是,甚至父母没有开口要求,有的孩子会自动上交自己的金钱:
一发工资,第一反应不是如何规划,而是给家人转账、买东西,直到账户上空空的,才会停止。
对于这种情况,付丽娟老师一针见血点出:
当我们不愿支配金钱,其实就是想通过上交一部分自我,来和父母保持长期的共生,回避自我负责。


还债的孩子
和拯救家庭的血包
这种系统共谋,会导致一个孩子通过这两种形式,在经济和精神层面掏空自己:
1、还债赎身
向我求助的好友,正是这种状态。
父母一次次的金钱索取,让她感到自己的是一个欠债的人。
父母发过来的一条条语音,就如同对她的房门大力敲击,不能忽视无法拒绝。
她向我抱怨母亲不顾自己两个孩子和高压的房贷,也抱怨父母曾经对她的忽视,
但这些痛苦她都无法直接对父母表达。
因为她害怕对父母再次失望——他们还是不爱我;
更害怕父母对自己失望——女儿没什么利用价值。
父母带给自己的痛太大,消耗太多,而滋养太少。
于是她产生了“一次性给一大笔钱”这个荒谬的冲动,来短暂推开痛苦的侵蚀,保护自己。
被亲情绑架的孩子,想要割肉还母削骨还父。
看起来很有力量,但这是一种具有悲壮感的幻觉。
这种“赎回自我”的方式,是通过“放弃自我”来实现的。
这个“给出去”的冲动,背后的潜台词是:
“行吧我不要了”
“我的主权不属于自己,还给你”

2、家庭的输血包、拯救者
功能不健全的家庭,长出一个有出息的孩子,这个孩子大概率会在经济上成为家庭的血包,精神上成为拯救者。
这样的孩子太多了,我自身也曾是这样一个角色。
我的父亲是个农民,年过70,母亲是多年的躁郁症患者,弟弟因为身体问题多年没有复工。
他们有出于本能的爱,但是功能不足。
我一个人在外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了10多年,每一次发展,都会带着内疚,因为家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如果家人不幸福,自己似乎也失去了快乐的资格。
于是,我定期汇款给家里生活;
在母亲抑郁发作期时,陪伴就医,情绪疏导;
也用各种形式关心年迈父亲和弟弟的身心。
长久下来,他们也习惯了这样的付出。
虽然我能挣钱,能养活全家,有自己热爱的事业……
但很长一段时间,我也被抑郁和绝望感淹没。
在心理咨询中,我讲述自己像个粮仓,但是没有门,别人总来这里搬走我的粮食,
导致我总也存不满,甚至有时空空如也;
有时也像一个漏气的气球,干瘪、没有弹性。
有时也像一只没有羽毛的鸟,散落在看不见的地方。
咨询师回应:
这么多年你都像是在给家人输血,
不仅要给钱,也要给很多关心。
那么,你自己呢?
我低下头,长久沉默。
看到自己被当成一个血包,是很不容易的。
血包是一个工具,而不是一个人:你不能有私心,不能有自己的愿望,不能停下来。
承认这一点很痛,但至少是真实的。
残酷的真实,让人生长出力量,来直面自己人生。
在长达一年的心理咨询后,我鼓起勇气和家人进行了一次深谈,坦白了自己的抑郁和无助,也提出了一个关于钱的方案。
幸运的是,父母很理解,也很内疚——“你最终还是要过自己的人生的”。
这种共同面对,打破了原有的系统共谋,让我的从家庭血包的角色,走向自己——
我是有能力供血,但我是个人,也会累,也需要支持照顾,也有自己的人生愿望要实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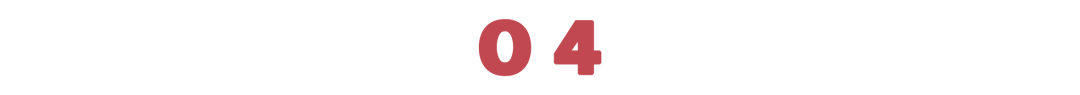
当好友向我讲述完自己的困境,我会心一笑,反问她:
你觉得这笔钱,谁是主人,谁更具有支配权?
她毫不犹豫回答我:我自己。
我看着她,点头肯定——是,你是钱的主人。
她在那一瞬间意识到了,自己给钱的冲动,背后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力。
一直以来,她都在这样做,以至于自己和父母都误以为:
她的钱,就是父母的钱。
父母的索取,不容她拒绝。
一次次无节制地给钱,本来是为了回避痛苦,却造成了更大的痛苦。
认识到这一点,她不再回避,开始直面和父母的共生纠缠:
她反问母亲,为什么只找她一个,而从不找弟弟?
她质问父亲,是否有看到她现在的经济困境,和她这么多年的付出?
这样的反问,是对原有的“系统共谋”,发起攻击。
其意义不只是钱,更是从共生走向分离,让自我诞生——
把自己的归属权从父母那里拿回,做自己的主人。
尽管好友和我,依然会给父母钱,但已然没有的之前的无力和绝望,而更多的是爱和能量的流动。
而这其中的改变,是一寸一寸发生的,并非一蹴而就。
能为自己说话,就是一份自主权的回归。
具体的操作方法没有万全之策,更重要是意识层面的改变。
失权的给钱和有自主意识的给钱,本质的改变就是——我作为人,不可忽视。
如果你也面对个人成长、原生家庭有困扰,渴求得以梳理和强有力的支持,这一次,不妨从武志红心理咨询中心的专业咨询服务开始——
在这里,你能充分地倾诉和表达,咨询师陪你一起面对你当下的成长课题,梳理脉络,找到问题解决的方向。
这一次,看见自己,开启你的心理咨询之旅吧~
点击下方卡片
👇👇👇
作者:陈轻轻。本文原创发布公众号:武志红(ID:wzhxlx)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