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作者 | 天雅
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——
一个在家常年负责做饭的老母亲,通常是勤劳、贤惠的象征。
但如果,一个女性长期被困在“做饭”的角色里,而没有其它价值来源,
那么她就有可能会利用这个角色来掌控厨房,掌控食物分配,掌控家人的饮食方式,以此获得存在的价值与意义。
从而导致家人在“吃饭”这件事上,处处受到控制和限制,失去原本的自由与乐趣。
事态严重的,还可能会引发厨房里的权力斗争和餐桌矛盾。
关于这一点,我的同事大森深有体会。

从大森记事起,母亲就是家中厨房里固定不变的“掌勺人”:
未退休时,她每天下班回到家,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厨房准备晚餐;
退休后,她更是每天定时定点地蹲守厨房,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。
但她并不享受下厨的过程,经常会在厨房抱怨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。
且母亲做饭有一个特点,喜欢“一锅煮”:
不管是蔬菜瓜果,还是鸡鸭鱼肉,统统混在一起煮,煮熟便上桌。
由于没有任何烹饪技巧,饭菜的口感自然也不咋地。
可母亲偏偏又对节俭有执念,餐餐都会“分配任务”,要求家人把饭菜吃光;
如果实在吃不完,她就会在下一餐将新菜旧菜混在一锅继续煮……

有一回,大森抱着体贴母亲、改善伙食的心态,提议让母亲歇息,由他负责买菜做饭。
母亲不乐意——
大森刚从外面买菜回来,她就抢着把菜拎进厨房,准备用她熟悉的方式进行一锅煮。
大森不得不将母亲从厨房“请”了出去,并强调他想亲自动手,让母亲在外面坐着等吃就好了。
结果母亲却浑身不自在——
每隔三五分钟就找借口溜进厨房,对大森的洗菜、切菜和炒菜方式指指点点,就差没抢过锅铲亲自掌勺了。
饭菜上桌后,大森吃着感觉还行,至少有点原本的菜味,而不是混煮串味了。
但母亲却一顿差评,抱怨大森青菜油放多了,猪肉炒得太干太硬了,嚼不动……
大森听取了母亲的反馈,并于次日购买食材,炖了一锅关东煮。
“肉质松软,味道鲜美,这回妈妈该满意了吧。”他心里想着。
结果母亲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两口,便以“吃不惯”为由,放下碗筷回房间了。
母亲的反应挫败了大森下厨的积极性。
而后顺理成章地,她又重新恢复了“掌勺人”的身份,继续一锅煮的固定菜式。

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,大森都无法理解:
母亲明明不享受下厨的过程,为什么却对做饭如此执着?
直到学习心理学以后,他才逐渐意识到:
母亲从年轻到年老,一直将自己固定在厨房里——
一边抱怨这是“吃力不讨好的活”,却又不允许别人替她完成这件事。
这一切,其实是缘于母亲内心深处对掌控感的依赖。
她通过掌控厨房、掌控食物、掌控家人的饮食方式,来获得一种存在感和安全感。
这种掌控,不是出于对下厨的热爱,而是出于一种“我必须在场”的执念——
她害怕自己一旦离开厨房,就会失去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力,甚至被边缘化。
而“一锅煮”这种看似随意的烹饪方式,不仅仅是对食物的处理方式,
也反映了母亲一种生活态度,反映了她内心深处对混乱和失控的抗拒:
将所有食材混在一起煮熟,她就不用面对选择和判断,更不用承担失控的风险;
哪怕味道不好,但至少是她熟悉的、可控的。

当大森抱着体贴母亲的心态,代替母亲下厨时,
母亲感受到的不是被解放,而是被剥夺——
她的反应不仅仅是对新烹饪方式的不满,更是对“失控”的恐惧,
她不断溜进厨房指手画脚,其实是在试图重新夺回对厨房的控制权。
她对大森做的饭菜进行批评,象征性地吃了两口就放下碗筷,
那既是一种对新食物的拒绝,也是一种自我保护——
她无法接受自己不再是那个“家里唯一能做饭的人”,更无法接受儿子可能比她更适合下厨。
她害怕失去自己的“掌勺人”身份,害怕价值被否定,害怕自己不再被需要。
她真正抗拒的——
不是儿子的体贴与反哺,也不是新烹饪方式带来新的食物口感;
而是她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被替代,以及自我存在价值的丧失。

透过心理学角度,大森其实能够理解:
母亲这种通过做饭来获得价值感和掌控感的行为,很可能跟她的成长经历有关。
在原生家庭中,母亲是家里的老大,下面有5个弟弟妹妹。
她的父母常年在外忙碌,于是照顾弟弟妹妹的任务,自然而然就落到了她头上。
由于长期缺乏被看见、被关心、被理解的机会,她只能通过照顾家人来获得价值感。
但这种照顾,又带着强烈的匮乏和控制性。

就像做饭这件事——
她并不享受下厨,但又害怕失去在家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,从而形成一种“强迫性付出”。
而一旦家人表现出“不想吃”、“想自己动手做饭”时,
她就会陷入失控的恐慌,想方设法让家人吃她准备的饭菜,阻止家人自己动手做饭。
当真正理解母亲这一系列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以后,大森内心充满了矛盾:
一方面——
他作为儿子,并不想跟母亲争夺“掌勺人”的角色,给母亲制造心理的恐慌;
但另一方面——
母亲对厨房强势的掌控欲,确实很影响全家的饮食质量,甚至有时还会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。
特别是在大森结婚以后,母亲依然充当着家中“掌勺人”的角色,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。
但大森妻子来自不同家庭,饮食习惯不一样,根本吃不惯母亲这种一锅煮的固定菜式。
一开始,妻子会礼貌性地吃几口,后来实在吃不下了,便自己下厨煮别的菜吃。
在一般家庭里,这可能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。
但大森母亲却无法接受——
她将媳妇的“不吃”和“亲自下厨”,视为对她固定“掌勺人”身份的挑战与剥夺。
于是她经常在大森面前抱怨媳妇饮食挑剔,浪费食物,并以“吃不惯”为由,拒绝吃媳妇煮的一切食物。
这一度令大森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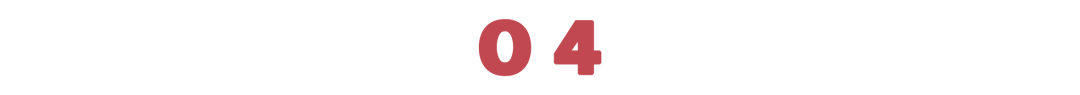
在咨询室里,大森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探讨母亲的一系列行为动机,尝试为家庭中越演越烈的“婆媳矛盾”寻求一个出口。
咨询师告诉他:
“你的母亲并不是坏人,她只是被困在了自己的心理结构中。
她的行为背后,是孤独、无助、对控制的渴望,以及对关系的渴望。
她需要被看见、被接纳,而不是被指责和纠正。”

为了将母亲从固化的心理结构中解放出来,大森后来做第一步就是:
坚定且温和地拒绝母亲的“强迫性付出”,将她从固化的“照顾者”角色中解放出来。
他知道母亲已经将自己未被实现的自我价值,都寄托在了厨房这个象征性的空间里,不愿轻易将“掌勺人”的角色交付出去。
所以他在跟妻子商量过后,选择了从家里搬出去,让自己先从“被照顾者”的角色中抽身出来。
当他刚向母亲宣布这个决定时,母亲陷入了失落与恐慌,害怕儿子有一天彻底不需要她了。
为了挽留儿子,她开始每天买卤味和炸鸡,那是她过去一直反对大森吃的“垃圾食品”。
大森看穿了母亲的意图,并坚定且温和地回应母亲:
“妈妈,谢谢您还记得我爱吃这些,但天天吃确实也不健康。
您放心,我已经长大了,以后想吃什么都会自己买/自己做,决不会让自己饿肚子。”
后来真正搬出去以后,大森和妻子正式开启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的自由生活。
同时他也会经常发信息问候母亲,努力让母亲感受到:
即便不再是一个天天蹲守厨房的“照顾者”,她跟儿子的联结还在,爱也还在。
奇妙的是,自从大森和妻子搬出去以后,他的父亲似乎也获得了某种心理的解放:
他开始经常带着妻子外出下馆子,品尝各种美食,既解放了妻子的双手,也解放了味蕾的自由。
写在最后
或许,这不仅仅是大森母亲的故事;
同时也是千千万万终日在厨房劳碌,却始终不被看见、不被理解的老母亲们共同的故事。
她们可能从小就生活在一种“必须付出”的环境中——
无论是为了家庭、为了孩子,还是为了维持某种稳定的状态,她们自觉承担起了“照顾者”的角色。
这种角色一旦形成,就很难被打破,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,更是一种心理认同。
大森与母亲的分离——
表面上是对母亲持续照顾和付出的拒绝,实际上却是对母亲自我存在价值的成全。
因为在一个家庭中——
爱不应该是一种任务,更不应该是一种控制,而是一种真实的感觉。
而在做饭这件事上,它更是一种允许自己选择做与不做的权利,一种允许家人选择吃与不吃的自由。
相信未来某一天,大森的母亲能够发现并体验到,厨房之外,还有更广阔的世界。
而她,并不需要刻意付出些什么,也依然能够是一个被爱、被理解和被接纳的人。
如果你也面对亲子养育关系、个人成长有困扰,渴求得以梳理和强有力的支持,
点击下方卡片
👇👇👇
天雅,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,广州心协三级心理咨询师,自体心理学长程在读。本文原创发布公众号:武志红(ID:wzhxlx)。
